作者:魏筱筠
在深水埗服務無家者大半年,通州街公園是我幾乎每天都會到訪的地方。這公園是九龍西最大最集中的一個露宿者聚居點,高峰時期住著上百位居民。他們瘦骨嶙峋的肢體彷彿被那些細小的針筒抽乾,扭曲的身形像微垂的枯樹。貧窮和病痛在我的眼前是具象的。
在搜索引擎鍵入「通州街公園」,一篇題為〈親子好去處—通州街公園〉的攝影網誌引起了我的興趣。
「住咗深水埗咁耐都唔知道原來有個咁大既通州街公園喺附近,不過我都唔太建議大家嚟,因為⋯⋯」
這位博主帶著兩個可愛的孩子在公園四處遊走,經過通州街天橋下的玉石市場入去公園,穿梭小賣部、噴水池、八角亭、波地、杜鵑花隧道,拍了許多照片。但是讀到文末,他卻在推薦語中建議大家「冇必要真係唔好去!」原因是「太多道友和露宿者,去廁所都撞見有人喺度打針,嚇死我呀!!!」。
腦子裡出現他說的畫面,我竟笑出了聲。
在深水埗一間社福機構工作了大半年,通州街公園是我幾乎每天都會到訪的地方,而這種道友打針的畫面對我來說已經司空見慣,沒有什麼可大驚小怪的了。
街坊和我
記得第一次踏足這個公園,是剛開始工作不久後的某個週二晚上。
因為第五波疫情在社區蔓延,大量的抗疫物資被送到了像我工作的社福機構。口罩、快速測試包、酒精搓手液,一波接著一波地湧來。如果不迅速將這些物資流轉出去,那麼不用多久辦事處可能連企的地方都沒有。
通州街公園是九龍西最大最集中的一個露宿者聚居點,高峰時期這裡住著上百位居民。它地處香港貧窮人口最集中的深水埗區,附近還有傳教修女會仁愛之家,元州街露宿者之家等服務露宿者的私營宿舍,通州街公園自然成了流轉物資的一處必經之地。
那次我跟著同事繞過一個一個破破爛爛的床墊,遠遠地遞上黃色單張,小心翼翼不讓自己和對方有任何身體接觸。他們瘦骨嶙峋的肢體彷彿被那些細小的針筒抽乾,扭曲的身形像微垂的枯樹。貧窮和病痛在我的眼前是具象的。
派物資的組織輪番上陣,通州街公園彷彿一個流動的劇場,每個角落都有故事在上演。公園的住客們,三三兩兩,打針、抽煙、食飯,不做什麼,應付我們這些源源不絕來關心他們的人。有人在呻吟、有人在睡覺、看手機,和我們平時無所事事的樣子並沒有太大分別。通州街公園的住客被公認的是被「寵壞」的窮人,但是他們仍然貧病交加,營養不良,眼窩很深,顴骨很高。
有人看見我們,會走上來和我們說話。
「可不可以幫幫我,我的消費券還沒有收到!」
「我的身分證不見了。可不可以幫我搞下?」
他們認得出,誰是社工,誰是過客,誰可以幫他。不久,我就和同事們一樣,稱這群人為我們的「街坊」。
我的職位叫活動工作員,英文是 Program worker,這是非政府機構聘用的無需專業資格的支援職位。這種職位緣起於2008年經濟逆轉下,社會福利署批了一筆錢招聘三千個臨時活動工作員,協助社署津助的非政府機構提升行政能力的同時,亦支援青年人就業。
在2014年政府即將結束整個計劃時,有一千多個臨時活動工作員面臨失業。其中一些人組織起來去立法會示威,抗議政府計劃短視,要求將這個崗位常規化保留下來。加上這些臨時職位在各機構中對社工的工作有巨大幫助,大大提升了服務質素,所以後來這種職位在很多社福機構中保留了下來,成為常設職位。
但是這個職位也是出了名的工時長、薪酬低並且難於升遷。如果想薪酬有大幅度提升,則必須修讀社會工作學位課程,取得註冊社工資格,這需要至少兩至三年時間,動輒二、三十萬學費。
城市冒險遊戲
每一天,我都會從社工那裡領到大大小小的任務。小到幫街坊買飯、買藥、買褲、陪診;大到幫街坊租屋、搬家、搵工、申請綜援和公屋等。此外,還有因應抗疫政策下的各種工作,帶街坊打針,送抗疫物資,幫街坊「搶」返深圳的過關名額等等。
我所在的這間中心主要服務四類人士:露宿者、更生人士、少數族裔和精神康復人士。這些人無論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是社會上最邊緣的群體,並且大多數人都缺乏支援系統。他們的共通點是:出生貧困,教育程度很低,原生家庭有各種問題,缺乏常態的人際關係,還承受著各種長期病痛或者身心精神健康的問題。很多人早已脫離了原先的社群,渴望隱蔽在都市的暗處。可是即使這樣,這個璀璨都市對他們仍然並不友善。
因為長期缺乏常態的社會和家庭關係,他們溝通能力不足,脾氣不好,說話不清楚,也聽不清楚你說話。有的人總是背著全部的家當在身上,有的人有嚴重酗酒或者藥物濫用的問題。
我的工作就是和這些街頭居民一起做任務,「玩」這個真人實景的城市冒險遊戲。
和這些夥伴一起做任務的時候,不僅要照顧他的身體,還要照顧他的情緒。要想辦法突破溝通的障礙以獲得關鍵信息,還要學習自我消化負面情緒。有時候還要和他一起承受各種被歧視的目光。
要想任務做得順利一點,有些小技巧的。比如早半個小時出門,搞清楚搭什麼車,每個區的社會福利署在哪裡,哪裡的銀行人少不用排隊太久,要見面的人最好提前打電話預約。但是即使做足功課,遊戲想要通關,多試幾次仍然是常態。
雖然隊友看起來總是漫不經心,可是通關的鑰匙卻往往也在身旁的這個夥伴。所以要學會沉默,學習觀看,練習等待,加上適時的鼓勵和催促,直到夥伴願意把通關的鑰匙遞給你。
分享幾個我的隊友。
阿嘜
露宿有群聚效應,不同類型的人會在不同地方聚集。除了通州街公園,尖沙咀海旁也是露宿者聚集的中心。在社協 2007 年出的攝影集《野宿二》中,有這樣一段描述:「背景是香港最賣錢、最美麗的夜景;四周沒有汽車廢氣沒有嘈雜聲;交通差不多是全港最方便,座落香港心臟地帶,要什麼接駁的車也有,偶然還會傳來古典音樂做配樂……難怪在香港文化中心露宿的,都叫這裡是「文化大酒店」。若與其他天橋底或路邊環境相比,這裡的露宿環境,真可說屬五星級。」
文化大酒店的居民很多是因為遇到臨時的經濟困境或者人際關係危機而在這裡住下。相比於通州街公園,這裡的居民彼此之間是相對疏離和獨立。有些是低收入的基層勞工,為了省下每個月幾千塊的租金,他們用揹包做枕頭、紙皮做床墊,放工後就來這裡和衣而睡。很多外籍人士也選擇在這裡露宿,阿嘜就是其中的一位。
阿嘜來自約旦,說阿拉伯語,是尋求庇護者,更通俗一點,他是個難民。
我們在 文化大酒店遇見了他,幫他租住了深水埗的床位房。這種房間,小小的一間有十多個床位,上下架,每個床位月租1500-1800元不等。相比於別的床位房,這一間剛裝修沒多久,租客還不多,並且業主承諾晚上會開冷氣,算是剛入職不久的我能接觸到的最好的房源。
入住當天,阿嘜就和業主發生了爭執。因為房中安裝了監控,阿嘜表示自己是租戶並不是囚犯,不能忍受這種被監視的生活。業主很委屈,從來沒有住客向他抱怨過這問題。安裝監控是出於安保原因,他本人幾乎從來不看,但是所有人都會因此更放心,所以二十四小時監控錄影是這種床位房如基礎設施一樣的存在。
沒過幾天又有新的衝突。我在半夜接到阿嘜的電話,他焦慮地告訴我房間太熱了,他睡不著覺。原來為了省電,業主一再限制開冷氣的時長。而隨著房間的住客愈來愈多,那裡已經悶熱難耐了。
對阿嘜來說,住屋並不是他最大的擔心。他最擔心的是被遣返約旦。他從認識我的第一天開始就不停地求我,讓我幫他去高等法院查閱他的卷宗,請求高院能撤回對他庇護申請的裁決。他用濃重的口音和激動的情緒告訴我,如果被遣返回約旦,他將面臨多麼可怕的酷刑和審判,即使身在香港也感受到強烈的不安全感。
另一件他擔心的事是注射疫苗。因為不久前做過手術,他很擔心打疫苗針令身體會有不良的反應。那時候是四月底,政府推行的疫苗通行證,要求12歲以上人士必須接種至少一針新冠疫苗,才可以進入街市、餐廳、理髮店等的「指明處所」。國際社會服務社的社工幫他預約了在佐敦的官涌體育館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打針,他求我陪他一起。接種中心了解到他是外籍人士,拿出了各種語言的疫苗接種手冊,其中有烏爾都語、印地語、法語、西班牙語等等,偏偏沒有阿拉伯語。我們只好一遍又一遍的向他解釋打針的流程,安撫他打完針會在觀察區休息十五分鐘,所以如果身體有任何反應都可以即刻送他去醫院。
最終他打了針。那日和他告別後我有一段時間沒有再見他。直到幾個月後,我帶新的街坊去租住那間床位房,才知道阿嘜曾經把攝像頭挪了方向,但是業主又把攝像頭挪了回去。和那裡的其他本地人住客一樣,阿嘜用布簾密不透風的遮起了自己這個狹小的空間。
兩位林布和一位丁生
林布是兩個尼泊爾人,他們都叫林布。後來我得知這是喜馬拉雅一支山地原住民的族名。因為疫情失業,他們交不起租,住進了「文化大酒店」。我們幫他們申請宿舍,申請綜援。
因為語言障礙,我對他們所知甚少。我不知道他們怎麼來了香港。但是和大多數受教育程度不高的本地基層男性一樣,他們從事倉務、地盤、保安、清潔的工作。即使在這裡生活了十多年,他們也不會說粵語,更談不上融入本地社群。
其中一個林布沒有結過婚,父母在尼泊爾過世多年。另一個林布有兒有女還有老婆,只是他們都不會來香港,而他也沒有錢回去妻兒身邊。林布 (們) 有自己的本地社群,但為了依附這個社群,他們需要付出的代價也不小。每月的綜援金,大部分都要上交掉。不是因為有人去世了,或是要隨份子錢 (賀禮紅包),就是被迫借給朋友有去無回。然後在剩下的時間裡,林布 (們) 會用酒精麻醉自己,在公用廚房裡煮米飯,一天只吃一餐度日。
今年已經六十多的丁生是在香港生活了幾十年的越南人,申請永久居民身分證的時候,福利署的公務員給他取了一個中文名。他是我們的老街坊,懂得有需要的時候在我們的辦公時間來找社工求助。他用社署的租金津貼在荔枝角道的一棟唐樓租了個劏房。獨居的他常年靠藥物來助眠,每個月數千元的綜援金都用來買鎮靜劑。我們幫他申請了公屋,登記了消費券,申請了樂悠卡 (長者卡)。
他年輕時做了許多年地盤工人,和許多像他一樣的男人一起,起了屯馬線。他告訴我很多工程都死了很多人,慶幸自己還活著;但是雙腿勞損仍要每天行八層樓梯對他來說很辛苦。他問我什麼時候公屋申請才有消息,根據官方統計,截至2022年6月底,公屋的平均輪候時間是六年。而作為單身男性,還要再長三四倍。我不知道他的公屋什麼時候才有消息。
雲誠咖啡吧
再來到通州街公園,這天這裡沒有派物資的人頭攢動。沒有警察,也沒有鏡頭。公園變得安靜和慵懶。在溫暖卻不刺眼的陽光下,貧窮、打針、殘疾和傷口變得沒有那麼可怕。
在八角亭的噴水池邊,我遇見了雲誠,大家慣了叫他阿誠。
很多年前,他曾經也做過街頭的居民,再之前,他是個經驗豐富的扎鐵工人。經營回收生意的原生家庭小富即安,可惜的是阿誠十四歲就染上賭癮,走上了一條起起落落的坎坷路。後來遇到嚴重的工傷意外,在治療後接受了福音,開始踢波,參加球賽,反反覆覆,最終戒了賭,又重新找回人生方向。
我認識阿誠是因為行山。他是機構行山小組的恆常義工,每隔兩周他會帶領一班年長體弱的街坊去郊遊。年過六十的他體力驚人,日行十多公里,每天穿梭在四分之三的香港;行完山還會回到通州街公園,參與各種類型的義工服務,義剪、派飯,是許多機構的在地聯絡人。
每個星期五的下午,他會在噴水池邊幫公園的居民沖咖啡。
「有咖啡、奶茶和熱朱古力,你要什麼?」
「我要咖啡。」 阿褲嘻嘻哈哈,來討一杯咖啡。「我一週都在等這一杯咖啡,喝了這一杯,才知道又一個星期過完了。」
在這裡生活
人們看這群公園裡、街頭上的居民,污糟邋遢、坑蒙拐騙、沒皮沒臉,精神恍惚,常常避之不及,但是和他們相處一段時間之後,我也看到他們的另一面。他們有喜有悲,有正義有幽默,也散發人性的光輝,對所愛的人極為溫柔耐心,對社群相互分享亦相互承擔。
來香港十三年了,我常常聽到長輩們說:「香港地搵食可不易。」那時候,我不想和這裡有長遠的關係,只在學校和家庭之間走動和生活。這份活動助理的工作卻似乎讓我多了一些留下來的勇氣。
我看到陷入最倒霉境地的人,也可以幽幽地低聲說出:「我真的沒錢交口罩罰款(沒錢交在行人路踩單車的罰款),你拉我坐監吧。」然後這個倒霉蛋輕輕吐一口氣,扔掉了法庭寄來的傳票,重新回到公園裡。
我看到又一次從監獄放出來的人,毫無辦法,只能重新踏上舊路,重複過去。但是他告訴我,他想找一間這樣的房子,其中一間給兩個人住,另一間給另一個夥伴,讓他們三個天涯淪落人可以一起生活。
在這片小小的土地上,承載了七百五十萬人的生活和夢想,很多事情,即使很小,也需要和幾個人分著做。有些人一輩子都住在同一屋簷下,為了一塊小小的空間,家人不和,親人反目。有些人遇到挫折,無法面對家人;也有人把空間讓給了家人,自己在街頭才終於能夠體驗獨立和自由的滋味。
不記得是誰,跟我說起了通州街公園以前的故事。
那時候居民們還住在公園外的天橋下。本來只想躲在城市的縫隙中寄居,卻因為周圍的地產發展,四處要起高樓,政府下決心清場,在天橋下圍起了柵欄,設起了路障和石塊,使那裡「長刺」,成了無法立足之地。
那一夜,天陰無月,無處安身的居民們帶著他們的傢什,跨越了紅海,進入了這美麗的應許之地,從此就住了下來。這裡的人彼此認識,相互照顧,在這裡休息,在這裡生活;彷彿他們從來就生活在這裡。雖然這生活在外人看來有許多問題,但畢竟這生活不是別人給的。他們已經在自己可以選擇和努力下,過上了對自己最好的生活。
對於曾經輝煌坎坷崎嶇的人生來說,他們也許從來不需要什麼救贖呢。
這些是我想告訴你的社區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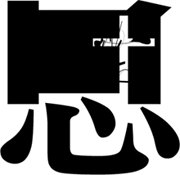

Pingback: 《思》第 146 期:我想講的社區 | 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