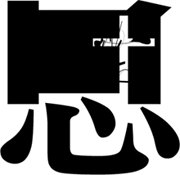「可以不說謊嗎?說真話就糟了!」這種「迷惑」竟成了社會上一股最活潑的力量。它一方面使人們失卻信心,失卻對為公義而戰的勇氣。反而得到的,是一種在自己利益以外的任何事情都一概不問的冷淡。謊言中帶出冷漠,冷漠導致順從,順從導致數之不盡的例行公事,而這卻被當作是「人就是這樣」的佐證,甚至進一步構成為人的「正常」表現。
文 / 邵家臻(香港浸會大學社工系講師)
打從發現believe中間隱藏著個lie字之後,我就在「真實」與「謊話」之間奔走。
煩惱。
幸好,不是每個人都如我般脆弱。
有的十分犬儒,認為所有真話在某程度上都是謊言。他們索性全身而退,專心做其「花生友」。
有的上下求索,以一副悲觀的眼睛,為人類生存的絮語和精神狀況的瘀青做出最深刻的闡釋。他們也質疑believe,詰問「戒律」,認為人類一面為自己塑造了無數戒律,但一面又因自己的盲目和脆弱,而永遠無法信守這些戒律,結果淪為「背信的動物」。
奇斯洛夫斯基 (Krzysztof Kieslowski) 正是這一種。
在群星閃爍的波蘭導演群中,早期的奇斯洛夫斯基並不特別起眼。在柏林圍牆倒塌之前的整整二十個年頭,奇斯洛夫斯基都埋首於紀錄短片之中,雖偶有佳作,但礙於共產黨的電檢制度和整體社會的封閉氣氛,使他的創作缺乏個性。直至晚年,他的作品才大放異彩,使他不僅成為歐洲最重要的導演之一,也使他成為二十世紀不可或缺的「哲學導演」。
1988年的《十戒》(Dacalogue) 本是奇斯洛夫斯基為波蘭電視台製作的十部每集一小時的電視影集。它卻完整地成就了奇斯洛夫斯基「道德虛無主義」的人生態度,以及一種「悲劇人文主義」的藝術風格。《十戒》當然不是一套宗教影片,也不是對「摩西十戒」的再詮釋。它只是一個藉口,一個反思「後解嚴時期」的波蘭人「不知為何而活」的生存處境,以及現代人失卻了上帝依靠之後的道德危機。政治一面無處不在,干預了一切,一面又無法提供任何解答問題的出路,身處這種厭煩的氣氛下,奇斯洛夫斯基索性將目光轉向個人,轉向個人的內心世界,轉向一個屬於個人最私密的角落之中。
摩西十戒之二:「不可妄稱上帝的名」。但基於對生命的尊重,人往往被迫以上帝自居。Dorota遇見治療她丈夫的老醫生,急切地詢問患有癌症的丈夫Andrzei是否有存活的希望。她需要一個肯定的答案來決定她是否保留腹中塊肉。原來,在丈夫大病之中,Dorota很想有個孩子,遂與一位音樂家發生婚外情,而且懷有身孕。她的情夫給她兩個選擇:生下孩子一起生活,否則墮胎分手。Dorota此刻希望老醫生給予答案,到底丈夫有沒有存活的希望。如果有,則墮胎與丈夫言歸於好;如果沒有,她就保留孩子。一時間,三個人面臨了極度艱難的道德困境:依據一個垂死的人的「生的希望」來決定一個新生命的「死的判決」,或者說,依據一個垂死的人的「死之必然」來決定一個新生命的「活的可能」。
兩個月後,Andrzei的病情逐漸好轉,Dorota決定墮胎,老醫生決定說謊。他告訴她,丈夫快會死去。老醫生違背醫德,違反戒命,以上帝之名作了假見証。可是,正因為老醫生的「違反」,所以保住了一條新生的生命。
誰能說老醫生僭越上帝之名是罪惡的?誰能說Dorota在青春將逝、喪夫在即,因而萌生要懷孕的念頭而發生婚外情是錯的?生活不就是一個謊言連繫著一個謊言的世界嗎?人生不就是從許多錯誤中走出來的嗎?當「誠實」面對現實的苦難時,它又能彌補些什麼?誰能說以上帝之名作出虛假的誓言而最終挽回幼小的生命是道德上的不可饒恕?奇斯洛夫斯基拋出了一個辯證的道德困境,一種關於「選擇之惡」與「生命之愛」之間的掙扎和苦衷,讓人無法閉目不看believe之中的lie成分,就算看後握腕輕嘆都好。
人文世界的believe與lie,彆扭迂迴,真是不能一句了得。政治世界常被認為是波譎雲詭,但believe與lie的關係,反而是「親者痛仇者快」得多。
講話沒有不重要;
鼓掌沒有不熱烈;
領導沒有不重視;
看望沒有不親切;
開會沒有不隆重;
閉幕沒有不勝利;
工作沒有不扎實;
進展沒有不順利;
完成沒有不完滿;
效率沒有不顯著;
人心沒有不振奮;
成就沒有不巨大;
問題沒有不是由歷史原因造成的。
就算發現了believe中間隱藏著lie這個密碼都好,大陸網民仍禁不住對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作出如此調侃。他們說,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生產了一種叫「新聞聯播體」,它像是一道填充題。新聞只要稍為改變一下人名等基本資料,其餘一切可以不變,照用如儀。
與其說內地網民對新聞聯播體的調侃是表明對中央電視台新聞報導手法的不滿,不如說是對這個謊言社會的不滿──什麼都不可信任,於是憤怒,於是犬儒。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發佈的2013年《社會心態藍皮書》稱,中國社會正出現負面情緒。仇恨、憤怒、怨恨、敵意等負面情緒與人民的需求不被滿足、人與人不信任和社會階層分化都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同時,中國社會總體信任指數跌破了合格線,人際不信任進一步擴大。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認為社會上大多數人可信。群體間的不信任加深和固化,紛紛表現在官民、警民、醫生與病者、普羅市民與商賈之間等社會關係的不信任之上。
回到香港,突破書誌Breakazine曾以《謊言社會》為題,總結了一百人眼中最荒誕的大話。它們包括:(一)爹親娘親不及毛主席親;(二)天安門廣場沒有死過人;(三)求學不是求分數!(四)政改方案更加前衛、更加進步、更加民主;(五)有承擔,真誠為香港;(六)李旺陽是死於自殺,證據確鑿;(七)今年七一有六萬三千人示威;(八)我的家裡沒有僭建;(九)有九萬人示威,即其他市民都是支持國教科;(十)我會攞住摺櫈,聽民意。當然,這只是2012年11月的事,若是今天再做同類的專題,如斯謊言,恐怕長賣長有。但調侃歸調侃,問題依舊在:一個自詡為政治家的領導人,能扛得住多少謊言?一個碩大無比的公務員體制,能扛得住多少謊言?一個動感之都,能扛得住多少謊言?一個最有前途的政黨,又能扛得住幾多謊言?一個正在崛起的國家,能扛得住多少謊言?我們都知道,因謊言而來的競爭力,是泡沫的;因謊言而來的公信力,是偷來的;因謊言而來的風光,是短暫的;因謊言而來的繁榮,是虛假的。
可惜的是,在上位者仍是明知故犯,仍然樂此不疲。說謊言作為生存策略,已由個人品德操守,極速發展至制度性現象。有「中國潛規則」之父之稱的吳思甚至警告,中國社會已成為一個善於生產謊言的體制。「在這樣一個說謊的收益很高、成本很低的制度下,從最高層開始,注定出現大規模的說謊。」他像是說,說謊這個行為已經離開了「劣行」的範圍,漸次成為活在這個國家的人必備的生存技能。
一個人,孑然一身,無法挽狂瀾於既倒,惟有以調侃作為反應。調侃,是因為他們仍然相信世上有真話存在。真話,這個字,今天聽起來像是個封塵的字眼,意思是,它代表了一種久被遺忘的老東西,更準確地說,它是瀕死的那一種。不過,有些人仍依稀記得,歷史上曾經有個年代,人們願意為「真話」而熱血奔騰,喊死喊活,甚至走上街頭,抗爭坐牢。那時的人大抵相信,這個世界真的有些東西完全可以超越個人生死而存在。他們不是不明白,在風雨飄搖的日子,聰明人都不應該放棄僞裝的本能。他們都被訓練成敏捷而深沉的獵人,耳聽八方,在幽暗的角落等待那許勝不許敗的一瞬。他們說,噓!我不是說謊,我只是隱瞞。在利用謊言與當權者打交道時,他們或許不知道,他們其實在為「謊言社會」助燃──謊言已經不只是一種劣質語言,它找到了自已的社會角色,甚至融會成制度的一部分。
吊詭的是,愈是集體說謊的時代,真話變得如斯稀有,它更加被視為最高道德原則之一。說真話的人之所以要有勇氣,正是因為他其實在展示一種不設防的姿態,一種邀請的手勢,像是大膽暴露自己在叢林中的位置,可能隨時遭受攻擊。但都顧不得那麼多,事關說真話的人都視真話比自己的安危重要。於他們而言,真話不是道德。真話是重建社會信任的一步。真話是一種抵抗暴政的政治力量。向「謊瞞騙隱的生活」(living in lies) 宣戰的,歷史上有過不少「個人」,但以政治運動鼓動集體行動的,當是哈維爾 (Vaclav Havel)。
那位在1977年發動了改變世界的「七七憲章運動」的發起人哈維爾,之所以對謊言深惡痛絕,是因為他並不以為說謊只是普通心理學意義上的那種特定的情緒。他所描述的說謊,則是活在威權主義下的一種更深層次的倫理狀態:時刻感到的,就是對「可以不說謊嗎?說真話就糟了!」的迷惑。他們彷彿看到一個無形的網羅縱橫交錯,所有點點滴滴的謊言最終都交會在一起。這是一個詭異的現象,絕大多數人在絕大多數時間裡,都不會親眼見到這個網羅,也摸不到它的絲線,然而,卻又意識到這個網羅具體地存在。它令你在生存與生活中都受到干預,而無需將你完全吃掉。這種干預最想消滅人家生命中自然和真實的東西,變成一種無休止的虛偽。結果,真正相信政府和無私地支持政府的人,其數量比以前的大為減少,但故弄玄虛者卻急劇上升。這不啻是叫人沮喪的局面。可惜,從政者很少去關心外表忠實的人民其內心真實態度究竟如何,也很少關心人民表態的真實性到底如何,就是有人走出來懺悔和坦陳,都不再有人關心他們所說的東西是否他們真心相信,還是僅僅是考慮自己利益而作出的一種表現而已。
這種「迷惑」竟成了社會上一股最活潑的力量。它一方面使人們失卻信心,失卻對為公義而戰的勇氣。反而得到的,是一種在自己利益以外的任何事情都一概不問的冷淡。謊言中帶出冷漠,冷漠導致順從,順從導致數之不盡的例行公事,而這卻被當作是「人就是這樣」的佐證,甚至進一步構成為人的「正常」表現。哈維爾要在lie中找回believe,以無限的天真和無限的勇氣,相信革命的底蘊該是場living in lies與living in truth的對決,是人們在希望與絕望、高雅與庸俗、真誠與虛偽、抗爭與恐懼、雞蛋與高牆之間,作出的一次歷史選擇。
歴史的結果如何?我不需贅述。我所關心的,是這個選擇又再降臨在今天。它站在我們的眼前,等候我們宣佈結果如何。